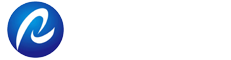文明史叙事与历史规律的探询
时间: 2024-10-07 21:11:45 | 作者: 开云官方在线登录
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规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以便更好地指导人类的真实的生活。近年来,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的历史理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回归。
在西方,书写有规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伴随基督教的出现,历史变为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摆脱了偶然和机遇”,历史进而有了“自己的规律”,但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理性、智慧、天意……天意指导并安排事件的进程,让它们奔向一个目标……历史首次被理解为进步”。
进入18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历史。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并出现了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图探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然和个别。
不过,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得东方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的意识被有意凸显出来,不但成为描绘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范畴,而且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奠定的全球秩序。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能力,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文明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
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把文明看作一个体系,认为文明史是一种有规律地发展的能动结构。他把人类精神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阶段。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世界历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进而指出,“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将成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
19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对欧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文明的普遍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吕克特在1857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中否认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即普遍文明的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会迈向统一的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出现危机,尼采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文明的定义以及文明发展的反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挑战了黑格尔的文明史观,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点。西方并无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权,“西方的没落”同样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也是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汤因比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是平行和等价的,并无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人类历史的发展将遵循多线而非单线的逻辑。受他们影响,西方学者不但摒弃了对文明的普遍主义研究,而且减弱了对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探询。
20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试图延续整体性、普遍性的文明研究思路,反思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但难以挽救宏大叙事式微之势。只有少数文明史研究,仍然保留宏观视野,推动着区域史和跨国史的研究。比如,布罗代尔在1963年指出:“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可以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而且,“任何与普遍性理论紧密关联的历史都需要恢复其线年代之后,出现不少气势恢宏、视角独特且颇具影响的全球文明史著作。这些著作强调“人类的沟通、交流以及移民”,内容大多根据研究主题或专题排序分类,侧重勾勒世界文明之间如何通过贸易、科技、移民、物种传播等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历程,但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定位以及未来前景问题缺乏一以贯之的解说,因而难以满足读者对总体历史和规律的追求。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它们无助于缓解我们对超越趣味性见解的简单汇编的强烈需求,我们渴望最终能够识别出全球历史发展的总貌。”尽管“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带来短暂的文明研究回流,但这类“文明话语的侧重点不是互联和互动,而是排他性和对文化特殊性的强调”。
总之,西方启蒙运动时代开创的以揭示普遍历史规律为目的的文明史研究,因不足以涵盖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受到力图挑战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学者们的质疑。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衰落的现实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文明史研究乃至对历史规律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作为全球通史的文明史叙事,过于强调跨文化的互动,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以及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规律却有所忽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长时段研究的再次兴起、普遍史的回归等史学实践的影响下,历史学家重燃对文明叙事中历史规律的兴趣。一些学者围绕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进行了重评,为历史规律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对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及其特征,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称谓,力图彰显这一概念在研究文明史中的重要价值。
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代”理论时,主要是想说明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可以在多个不同地方实现突破,而不是只在西方一处实现。再者,有别于19世纪的地域文明研究,雅斯贝尔斯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形成特有的“文明复合体”。与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文明作为历史哲学的思辨构想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倡导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阐释。
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和规律的探究,体现在围绕轴心时代文明“突破”标准的争论上。他们的基本共识是,文明观念的“突破”源于人们特定能力的出现,而非一般意义上物种演化的必然结果。“就最基本层面而言,认识转型与围绕人的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阐释相关,具体来说,与人的反思性、历史性、能动性相关。”由此,避免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世俗化、文化同质化。多元现代性,进而成为学界最有影响的“文明话语”。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历史规律研究的重新关注,主要是未解决当下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困境,进而尝试提出一种对西方文明发展规律的新的解释。具体来说,西方文明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危机。
其一,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并未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反而积弊甚深,甚至积重难返。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危机来自资本主义的危机,来自西方文明内部贫富的两极分化。西方文明几乎丧失了理性设想未来全球秩序变革的能力。
其二,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减弱,并由此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文明实体本来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发展快慢和先进落后的相对差异,并在事实上形成某种文明的中心地位。进入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当成维护自己优势地位、推进和扩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但是,当西方国家的全球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逐渐丧失中心地位时,全球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正在面临被非西方新兴大国追平或赶超的可能,近代以来形成的“东方从属西方”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更有西方学者指出,新冠疫情只会加速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文化精英意识,遮蔽了他们探究全球失序原因的真正方向。
其三,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挑战,如全球公共安全、气候危机和生态灾难、全球治理难题,这些迫使西方学者去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及人的存在等终极问题。以“人类世”概念的提出为例,这一概念逐渐被科学家和大众接受,意味着有必要把人类置于地球乃至宇宙演进背景下,考察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这类整合人的历史与环境的历史的文明史,要求历史学家关注全局性、长时段的发展演变规律,体现出对“人类社会如何变迁”“现代社会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的深刻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此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效应、合成生物技术等,也不断冲击着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固有理解。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用传统的人性论、文化本质主义或科学技术决定论已经很难解释文明演进和社会变迁。不少国家倡导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作,采用综合性的视角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人类的文明及其发展规律。
通过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与危机,西方学者试图重建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进而为经历急剧变革、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西方人找回历史发展中的确定性。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文明史叙事中关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仍然要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人类历史与环境历史的整合中弥合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争论。第二,如何在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同时又不陷入多元折中带来的万能和万不能的解释陷阱。对于西方文明史发展规律的探询,若要求得好的发展,就必须在“终极原因”或“根本动力”的理解和解释上进行一番革新。170多年前,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动了历史本体论革命,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论,仍然不失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