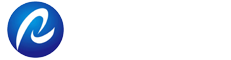【48812】黎世泽专栏|故土旧韶光③板车记
时间: 2024-09-03 07:36:57 | 作者: 云开平台
幺伯是石匠,那时正年青,在石堂里打石头,抡起大锤,像电影里慢动作相同慢慢地抡过头顶,崎岖有致地吼:“嘿咗——嘿咗——嘿——咗——哟——”声响从这边山传到那儿山。大锤在头顶停一停,然后,猛一锤击,击着石头上的锲子,击得火星飞溅。他不知疲倦地抡锤,抡锤出一块块整规整齐的条石。当石堂里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条石,便一块一块地运到乡上。乡上的供销社、食物站、茧站、粮站,乡上的许多房子都是这些石头砌成的。

幺伯用板车运石头。板车运石头便是拉板车。幺伯将条石掀上板车,放于车架中心方位,然后,肩上套住粗粗的拉绳,双臂夹住粗粗的车把,一声“起”,拉着板车出石堂。石堂外是慢慢的下坡,幺伯双脚用劲一蹬,板车快跑。幺伯悄悄腾空,假势快滑。板车冲上慢慢的斜坡,幺伯身体前倾,绷紧拉绳,抓住车把,顺着惯性,板车轻松跳过坡顶。在平路上,幺伯站立笔挺,稍带拉绳,稍抚车把,板车吱吱嘎嘎,平稳前行。到了峻峭的坡道,幺伯斜斜前倾,脑筋就要着地;拉绳深深陷进,肩头就要分裂;车把紧紧抓攥,手臂鼓胀,脸颊紧绷,筋脉偾张,汗水渗冒。幺伯一声“嗨哟”,板车一声“吱嘎”,一前一后,一摆一晃。又下斜仄的坡岭,幺伯拼命后仰,双臂夹紧车把,双脚死死驻地,光着的脚趾抠进泥里,车尾的刹车木划出深深的印痕……
幺伯与石头打交道,与板车作同伴,走在宽广的财源,家里就有结余,手头就有宽余,日子就有充裕。幺伯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幺伯喜爱打石头,喜爱拉板车。
但,幺伯不能打石头不能拉板车了,他的膝盖被石头碰碎了。他没有拿打石头拉板车的钱去找医师,他舍不得花钱,便和我爷爷把桐子米捣烂,搅拌红糖、白酒,厚厚地敷在膝盖上,肿得发亮的膝盖敷成了小山包。敷着药包的幺伯,在屋前的椅子上,久久地长坐,深深地叹息,叹息声传荡在幽邃的傍晚里。他很惦念他的石头,他的板车。
幺伯的板车停在路旁边。那是从石堂衔接乡上的板车路。我那时喜爱处处游玩,特别爱在那板车路上散步。板车路宽宽的弯弯的,跳过山坡,绕过人家,顺延水沟,转承沟湾。沟湾的岩壁上一排排规整的墓洞,像时刻的白叟注视着无尽的落日。水沟的上头连着一座大水库,干旱时节流动嚯嚯的活水。我喜爱板车路,顺着板车路能够到乡上,乡上有大礼堂、邮电所、理发店、供销社,有打铁铺、榨油坊、加工房、发电房……能够看电影,能够看打铁,能够看榨油,能够买想用的想吃的……幺伯呢,顺着板车路,能够打石头,能够拉板车。我看见板车路上的幺伯,洒脱的姿态,拼命的劲头,曲折的身影……
在暮色苍茫中,板车路弯曲飘绕,若有若无。板车静静地停靠,后边车架着地,前头车把朝天,两只车轮分立两头,像静静蹲屈的孤寂落寞的幺伯……
那是随爸爸去镇上送公粮。那时乡上还没有粮站,送公粮就得去二十里外的镇上,开端用扁担挑,费时吃力,还得去屡次,后来借得他人的板车拉,省时省力,一次就可搞定。
麦子收割后,爸爸把送公粮的麦子一袋一袋地装好,搬上板车,一大早就向镇上拉去。爸爸肩上套着拉绳,双臂夹着车把,身体腾空,双臂下压,脚尖踮地,“起”,沉重的板车“吱嘎”摇晃,慢慢跋涉。上坡的时分,爸爸身体绷紧,肩胛高突,腰部歪曲,一步一步,缓慢匍匐,我就在后边用力地推,支撑加力。到了平路和下坡,爸爸叫我坐上板车。但板车上堆满麦子,很是沉重,我为爸爸忧虑,不愿上去。爸爸说:“没事的,上去吧。”我便爬上板车,坐在高高的麦堆上。
到了平路和下坡,爸爸公然就很轻松。我看见爸爸稍稍笔挺,稍带拉绳,稍拽车把,双替,不急不躁,板车吱吱嘎嘎,平平稳稳。五月的太阳已很毒辣,我和爸爸都汗流浃背,炎热不已。爸爸便稍稍加力,起势跑起,凭借板车,顺着惯性,时而腾空,时而触地,时而跌宕,时而蹿跃,轻盈愉快,像宅院上空的老鹰飞掠。如此跋涉,板车既跑得舒畅,爸爸也得到歇息,就爽快得多。我坐在板车上,两旁的树木、房子、山峦纷繁后退,耳旁清风阵阵风声呼呼,跟着板车的腾空闲逛,我似乎腾云驾雾一般,飘在云里,飘在雾里。
爸爸忽然双脚驻地,车把上扬,一下慢了下来,是躲避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车。大车像一座大房子,高得很,长得很,我仰起头才看到车顶,走了好一瞬间才从车头走到车尾。大车上坐了很多人,他们都古怪地望着我,我也猎奇地望着他们。
来镇上送公粮的人很多,咱们走拢粮站,前面弯曲折曲地排着很长的部队。咱们送完公粮,天就快黑了。爸爸拉着板车回走,要我坐上板车。我在板车上,一瞬间腾空,一瞬间飘摇,看着血红的落日落下山坡,看着洁白的炊烟飘飘绕绕,看着远处的群山苍苍苍茫,看着两旁的树木、房子、山峦在暮霭中逐渐含糊。回到家的时分,我在板车上睡着了,爸爸把我喊醒,我感到一阵清凉,本来我的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露珠。我揉揉眼睛,在睡眼蒙眬中问爸爸:
“咱们家的茅草房该拆了。”在不知多少个清晨和夜晚,妈妈和爸爸叽叽咕咕的声响,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他们商议着修房的事:修房就修瓦房。
修瓦房就得烧瓦。我家烧了一大窑青瓦,一家人用箩篼担、背篼背,但箩篼担了几挑,背篼背了几趟,就把人累得趴下,爸爸便借来板车,咱们咱们一同着手,把青瓦一摞一摞堆上板车,车架上堆得满满的,一车青瓦有好几箩篼、好几背篼。
爸爸便肩套拉绳,张开双臂,悄悄跃起,双腋夹住高翘的车把,一把按下,然后,双手紧握车把朝前扯动几步,到了一个斜坡,立马车把上扬,身体后倾,双脚用力驻地,一步一步下了坡,转一个大弯,到了平地,他后倾的身体一下前倾,就平顺地拉动了。堆积如山的青瓦压着板车吱吱嘎嘎。爸爸那时年青,很有力气拉板车。板车轻松自如地来来,一大窑青瓦就轻松出窑了。
那时,土地下放了,人们像伺候月母子相同伺候自家的土地。但庄稼遍及成色欠好。乡上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土角,哇啦哇啦地吼:伺候月母子便是要让月母子吃好,伺候土地也相同,也要让土地吃好。化肥很有养分,人们便将化肥喂到土地。但那时化肥紧缺,并不常常买到。在那个栽秧时节,我家托人在二十里外的镇上买到了化肥,让爸爸和妈妈快乐得合不拢嘴,却又感到忧虑,几大袋化肥好几百斤怎么弄回来?担吗?背呢?对了,有板车。爸爸和妈妈便拖着板车到镇上拉化肥。
在学校外面的公路上,爸爸和妈妈拉着板车走过。那几天下过雨,板车深深地陷在泥泞里。爸爸肩套拉绳,手攥车把,在前面拉。妈妈手扶车轮,依托车架,在后边推。他们屈伸前倾,身体紧绷,像顽强不平的老牛。他们萧规曹随,一步一拽,像缓慢蠕爬的蜗牛。他们趔趔趄趄,几欲跌倒,像浑身糊泥的泥人。那时,我坐在教室里,教师在讲台上一字一句地教学同旁内角的解题方法。我的眼睛忽然转向窗外,看见泥泞里两个了解的身影,不由瞬间流泪。教师对我怒发冲冠:“开小差,站起来!”
在泥泞里拉化肥的爸爸和妈妈,没有让泥泞浸湿化肥。板车,让爸爸和妈妈避免了重复往复之苦。板车拉回的化肥,完好无缺地喂进了稻田。那一季,我家的禾苗长得特丰茂,特健壮。
说是我家具有并不精确,应是和他人共有更为切当。那是爸爸和村里的饶石匠一同做了一架板车。
饶石匠也像幺伯相同,处处打石头,处处修房子。他在石堂里把打好的一块块石头,运到修房子的当地,石头太沉太重,一块要四个壮劳力架起小牛,才干“嘿咗嘿咗”地抬走,费时吃力,便想起板车拉这个省力方法。板车拉石头,只需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边推。在好几个傍晚,他来找到爸爸,和爸爸叽叽咕咕地商议,想和爸爸一同拉板车。那时,爸爸愁闷着钱呢,饶石匠的到来,很受爸爸欢迎:有力使,有活干,有赚钱,好呀。
板车,相传为鲁班发明。板车以两个车轮为标志,省力首要就在两个车轮上。据考证,上古时代的运送全赖手提、头顶、肩扛、担负、橇引。后来,又以马、牛等驮运。跟着社会发展,逐渐发明出滚木、轮和轴,呈现了车这种运送工具。原始的车轮没有轮辐,这种车轮在古代称之为“辁”。夏代前后,呈现了无辐条的辁和有辐条的车轮。汉代陆贾在《新语》中说夏王朝“车正”(车辆总管)奚仲“挠曲为轮,因直为辕”,发明了有辐的车轮。由辁发展到轮,使车辆制作发生了大变革,为鲁班造车奠定了坚实的根底。
鲁班的造车技能一路延传,几千年后也传到了爸爸和饶石匠的手里。爸爸和饶石匠买来一根手腕粗的铁轴和两个大大的轮胎;搬出几根柏木,请木匠做了一副长形车架;车架左右粗大健壮的纵木,前延三尺,渐朘稍圆制成车把;取出几把麻线,合股搓成一条粗实的拉绳。
在一个月明的夜晚,爸爸和饶木匠将铁轴、轮胎、车架等部件,一件一件地迎合,相同相同地匹配。然后,在车架后边的横木上钉上一截短木,作为刹车木。最终,在车架前端的横木上套上拉绳,板车就功德圆满。爸爸和饶木匠急不可耐,先要试试,便轮番拉着在地坝里转圈。板车沉稳,轻捷,车轮滚动,吱吱欢唱,乐律美好。他们转了一圈一圈,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快乐得像孩子。
爸爸和饶石匠出去拉石头了。饶石匠那会儿在东边打石头修房子,他们就去东边。在雾气袅绕的清晨,我看见他们出了门,一个扛着车架,一个扛着铁轴和铁轴两头的车轮,一前一后,一晃一悠,淌过田坎,淌过沟湾,淌过山坡,消失在苍茫的山野里。晚上,爸爸回来了,他的右肩上有一大路深深的红印,还渗出斑斑血迹,那自然是板车的拉绳勒出的。在东边拉了十天半月后,爸爸快乐地攥着一大卷钱回来,一个劲儿地说人家的好:“石头一拉完,就结钱,哎,真是直快人呀。”爸爸拉板车拉来的钱,我和妹妹的膏火、书费、簿本、笔有着落了,全家的锅、灶、碗有润泽了,地里的肥料、种子、农药有出处了……爸爸拉板车拉来的钱,一眨眼,又去了另一个当地。但,爸爸有拉不完的力气,有拉不完的板车,有拉来的一卷一卷的钱。
爸爸去了东边,又去西边;去了西边,又去南边;去了南边,又去北边,在东南西北,在远远近近,都拉板车。板车在坡路上,在斜路上,在平路上,在岩嘴上。板车在晨雾里,在中午里,在傍晚里。板车在盛暑里,在寒霜里,在风雨里。板车上坡,下坡,平行,转弯。板车吱吱嘎嘎,砥砺前行,歌吟颂唱……
那个冬季,爸爸在北边的叫花坟拉板车,天天一早出去,晚上回来,在冰冷里只穿薄薄的单衣,还被湿透了,那是拉板车被汗水浸湿的。爸爸那阵很高兴,连连许诺:这次领了工钱,在腊月给我和妹妹买新棉袄和橘饼糖。咱们喜爱扎实的新棉袄,抵挡刺骨的冰冷。咱们垂涎甜甜的橘饼糖,我知道,妈妈每次带我和妹妹去外公外婆那里,都要捎去橘饼糖,外公外婆喜爱橘饼糖,但他们知道我和妹妹也喜爱,他们常常只尝一点点,就塞到我和妹妹手里了。
爸爸在叫花坟拉了二十几天,能领不少工钱,但拉完石头那时没领工钱,主人家说腊月里给。但腊月到了,腊月又要完了,眼看就要春节了,仍是没有领工钱的痕迹,爸爸和饶石匠相约去问问。天上飘着雪花,北风长号吼叫。我和妹妹望着爸爸和饶石匠在迷蒙中走去,咱们盼着他们快快回来,回来就能买新棉袄和橘饼糖。傍晚时分,爸爸回来了,浑身是雪,却两手空空,我和妹妹眼巴巴期望的新棉袄和橘饼糖,落空了。
爸爸和饶石匠去到叫花坟,看见修房的那家在半途停下了。那是起屋梁的时分,房子垮塌了,三个人从房顶摔下,死去一个,两个躺进医院里。那家的大人整天在外处理后事,只要两个小孩蜷缩在屋,屋是晒席搭成的窝棚。
其实,爸爸从叫花坟回来,去了供销社,买了新棉袄和一大包橘饼糖,箭步地朝家里走,走着走着,折转又去了叫花坟。那时雪下得好大,风刮得好凶,窝棚上一片洁白,窝棚里北风阵阵。小孩冻得挤作一团,声声啼哭,阵阵啜泣,他们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爸爸把新棉袄和橘饼糖放在了窝棚。
爸爸说,过了正月初几,又要出去拉板车,拉了板车领到工钱,给咱们买新棉袄,给咱们买橘饼糖。